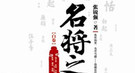一生从未打过败仗的“杀神”白起是怎么死的?
- 作者: 本站编辑
- 来源: 全息网
- 点击: 1363
时间: 2013-03-19
核心提示:
文章摘自《名将之死》 作者:张锐强 出版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公元前262年,白起带领秦军,占领了韩国的野王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。这样以来,韩国的上党郡与国都,就中断了联系。因为韩国的都城在新郑附近,从上党郡到新郑,必须从野王渡黄河。韩国打算献出上党郡,请求秦国退兵,但是上党郡的太守冯亭,却另有打算。他说:“不如投降赵国。如果赵国接受上党,秦军肯定会派兵攻赵。赵国受到攻击,自然而然地会跟韩国结盟。韩赵联手,击败秦国才有希望。”说干就干,他立即派人到赵国,请求派人接收上党。这是天上掉下来馅饼,还是烫手的山芋?赵王拿不定主意,就把平阳君和平原君叫来商议。平阳君说:“强秦在后,怎么能要呢?贸然接受上党,祸患肯定要大于收获!”平原君赵胜,也就是公孙龙的主人,意见正好相反。他说:“要占领一个城池,得费多少军马钱粮?现在人家白白送上门来,我们再不要,不是傻瓜吗?”
赵王也是个贪心的家伙,竟然同意火中取栗。他封冯亭为华阳君,让他继续坐镇上党。这一下,可是摸了老虎的屁股。公元前260年,左庶长王龁统率秦军进攻上党,上党居民为了躲避战火,纷纷逃向赵国,赵国立即派出军队赶到长平一带,安抚接应逃难的百姓。
秦军和赵军,就此对峙于长平,也就是今天山西高平西北一带。赵军的是名将廉颇。有一天,秦军的侦察兵跟赵军不期相遇。既然是侦察兵,兵力肯定不多。赵军希望占点便宜,于是主动发起攻击。结果呢?秦军虽然人少,但战斗力并不弱;一战下来,赵军大败,还损失了一员偏将。后来两军又打了几仗,赵军接连吃亏,丢失了两座营垒,和几名都尉。廉颇见秦军势大,就下令采取守势,不准部队出战。
秦军远来,利在急战。赵军这样老拖着,秦国可不愿意。但是赵军有四十多人万,秦军的力量也超过六十万。六十万人马就那么耗着,后勤补给线那么长,每天要消耗多少粮草?你当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朝前线运,可是那些粮草,只怕有一大半,要被役夫和骡马在半路上吃掉。而且时间越久,各个诸侯国合纵攻秦的可能性就越大。
一句话,夜长梦多。
怎么办呢?范雎两条腿走路,一手抓和谈,一手抓战争。和谈当然是假的,当时赵国派了使者过来,范雎下令,大张旗鼓地厚待赵国的使者,三天一大宴,五日一小宴,对他恭恭敬敬,无比殷勤。范雎这么做,是想给其他国家传递一个假信号:秦国和赵国正在和议,双方谈得很融洽,用不了多久就会罢兵,咱可不能蹚这道浑水,免得落个里外不是人。至于作战,范雎的主意更馊:离间计。他派人带着许多金钱作为活动经费,到赵国的国都邯郸大造舆论,说:“秦国不怕廉颇,他早晚会投降的。我们只怕马服子赵括。要是他出来带兵,秦军就麻烦了。”
#p#副标题#e#这些流言蜚语,很快就传到了赵王的耳朵里。赵王对廉颇,早就有一肚子意见。为什么?因为赵军连吃败仗,廉颇却老是坚守不出,这个态度,赵王不喜欢,因为形势也不允许赵军拖延。赵国的军粮一直供应紧张,派人到齐国借粮,齐国又改变了外交政策,不掺和西方的战事,希望埋头发展,积蓄力量。
士兵们没有吃的,必然会引起骚乱。因此赵王万分着急。他多次派人到前线申斥廉颇,可廉颇呢?你有你的千条计,我有我的老主意,油盐不进。
赵王的耳朵根子没那么软。这些流言蜚语,只是推动了他一下,坚定了他走马换将的决心而已。他随即下令,启用赵括前往长平,代替廉颇。
消息传出,秦王大喜。敌变我也变。他马上给白起一道兵符,命令他火速赶到前线接替王龁。为保密起见,他同时设置了一条高压线:“谁敢泄露这个机密,斩!”
却说赵括,对这一切全都蒙在鼓里。他当然明白赵王为什么要启用自己,因此一到前线,立即不折不扣地按照上级的意图部署。对原先赞同廉颇做法的将军,不换思路就换人,大批撤换,积极部署进攻。
白起深知,四十多万赵军并不是软柿子,可以由着他捏。要是他们还躲在坚固的营垒后面,不出来接战,那他就是老虎吃天,无从下口。
如何抵消赵军营垒坚固的优势?白起决定引蛇出洞。他派一支弱旅,担任诱敌任务,到赵军营门前挑战。等赵军出来,他们略微抵抗一阵,转身就逃;派两万五千精兵,切断赵军的后路;另外骑兵五千埋伏在半路,以最快的速度楔入追击的赵军中间,将他们切为两段,以便各个击破。
就战术而言,这是份近乎完美的作战方案,非常专业。能否成功的关键,在于赵军是否出来追击,而是骑兵能否坚守住阵地,真正切断赵军的联系。要知道,真正打起来,他们将两面受敌。这五千骑兵,也许会成为赵军的夹心饼干。
一切部署停当,当年八月的一天,秦军开到赵军大营前挑战。这正对赵括的胃口。他披挂整齐,点齐人马,出去接战。结果没打多久,秦兵就败退而去。机不可失,赵括哪肯放弃,他一挥佩剑,赵军随即呐喊着追了过去。
秦军且战且走,一直退入大营。赵括见秦兵如此不堪一击,越发来了情绪,挥动令旗,三军随即摆好阵势,攻击秦军的营垒。
白起早已做好准备。数十万秦军严阵以待,赵军仓促之间,哪里攻得下来?正在这时,一个哨探匆匆跑来:“报!启禀大将军,我们背后出现了一支秦军,已经截断我们跟大营的联系!”
赵括并不是传说中的书呆子。他自幼熟读兵书,虽是第一次指挥作战,但面对如此险情,并不惊慌。他立即传令停止攻击,前军监视大营的秦军主力,后军转身,猛攻楔进来的秦军骑兵。同时派人赶回大营,命令他们,从背后策应。
赵括冲锋在前,两军血流成海。赵军士兵知道局势不利,在主帅的激励下,作战非常勇敢,但奈何那支秦军,死战不退,怎么着也冲不开道路。
赵括当机立断,再度改变部署。命令外围的士兵掩护,里面的士兵放下武器,拿起工具,修筑营垒,坚守待援。就这样,局势暂时得以稳定,但四十多万赵军被分成三截,首尾不能兼顾,情势万分危急。
到九月,赵括被包围已经整整四十六天。赵军本来就粮草不济,这是赵王着急决战的重要原因;现在大军被围,粮草运不进去,士卒们更是没有一粒粮食吃。在这四十六天里,赵括并没有坐以待毙,一直在组织突围。他将士兵分为几队,轮流出击,但到底也没能突出秦军的包围。
没有粮食,第一步杀马,第二步就是吃人。战死的士兵尸体,马上就会被抢着吃光;吃到最后,受了伤不能动弹的士兵,也成了战友们的盘中餐。赵括坚持的这四十六天,白起同样如坐针毡:将士连日征战,疲惫不堪;补给一直紧张,要不断催粮派款。作为经验丰富的统帅,他深知要对赵军实施最后的毁灭性打击,他手下的人马,显然不够,因此使者络绎不绝,求援文书不断地朝咸阳飞去。
这个局势,显然秦王也是头一次碰到。秦赵两国,都是举全国之力,苦苦坚持。这是两国之间的决战。秦王不敢怠慢,亲自赶往河内,就是刚刚从韩国手中夺过来的黄河以北地区,将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子,全部赐民爵一级,然后编组成军开赴长平,负责截断赵军与国内的联系,彻底切断他们的粮道。
#p#副标题#e#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支援,赵国呢?根本派不出一兵一卒,除非不要针对匈奴的边防,将李牧的大军也调来前线。这当然是不可能。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,好有一比:医得眼前疮,剜却心头肉。
最后的时刻到了。赵括强打精神,撑起虚弱疲惫的身体,披挂整齐,亲自带领临时挑选出来的,还能勉强支撑的士兵,突然冲出营门,朝秦军扑去。成与不成,反正这是最后的一战。
秦军的连弩非常有名,大家想必都在电影《英雄》中见识过。将军们一声令下,矢如雨飞,赵括身中数箭,大叫一声,倒地身亡,壮烈殉国。看到这里,谁还能指责他是个书呆子呢?他绝对不缺乏军人的能力,素养,以及血性。
主帅阵亡,又断粮多日,包围圈中的赵军,迅速土崩瓦解。按照《史记》的记载,四十万赵军被俘。他们的命运会如何呢?华阳之战中那两万赵军俘虏的结局,已经做了极其强烈的暗示。白起说:“上党的百姓,宁愿归附赵国,也不跟随秦国,赵国人肯定更加仇视秦国。他们向来反复无常,留下是个祸害。”于是下令,全部活埋,只放掉二百四十个年轻的士兵,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子,回邯郸报信。
经过多次激战,俘虏四十万这个数字,可能偏高。也许二十多万,比较合适。因为根据《史记》的说法,这一仗,赵国共损失四十五万人,而白起自称秦军阵亡过半,也就是说,有三十万人战死。在战场上击毙五万赵军,无论如何,也不会造成秦军这么高的阵亡率,否则战争的最终结局,必然会改写。考虑到秦军处于攻势,伤亡率高,二十万对三十万,基本靠谱。
四十万也好,二十万也罢,这两个数字同样惊人。无论如何,白起应当对这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。毫无疑问,这是他身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,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他为“人屠”。但是,我不赞成拿现在的价值观,去套历史人物。任何历史人物,无论他多么英明,也无法脱离当时的时代,正如你不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。作为秦国将军,白起要考虑的是如何削弱敌国的战斗力。这几十万人一旦回去,不久就会再跟秦军刀兵相见,别说白起,就是白痴,也能想到。不仅如此,秦国一直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,提倡严刑峻法。如果不杀也不放,先扣留着,这几十万张嘴都要吃饭,也够白起受的。所以白起的决定虽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,但也有他自己的道理,符合他作为百战名将的一贯逻辑。借用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的一句话: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。如果我们一味苛责他,谁能保证这样理直气壮、预设道德正确的责难,将来不会沦为笑柄?
白起活埋赵军俘虏四十万,若干年后,也在新安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渑池,活埋秦军降兵二十多万,所持的逻辑如出一辙。唯一不同的是,秦兵内部确实不甚安定。因为东方各国人服徭役进入关中时,经常受到秦国官民的欺侮凌辱,现在有了机会,诸侯联军自然要趁机报复,时不时地要羞辱他们一顿。那些降兵心怀疑惧,私下里议论纷纷,埋怨带领他们投降的主将章邯。项羽的脾气,大家都知道,想让他采取妥善的办法消除摩擦,做“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”,那可比登月还难。他一拍脑袋,下令发动夜袭,把那些秦兵全部活埋。
有组织有策划的大规模屠杀,白起和项羽,并非特例。在中国,还有唐朝末年,黄巢荼毒陈州,明朝的血洗四川,以及清初多铎制造的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;在国外,在卡廷森林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,日本人制造过南京大屠杀,希特勒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。这些方式比起白起和项羽的活埋,更不节能更不环保,也更加凶残无道。
巧合的是,秦朝和项羽的政权,几乎同样短命;白起和项羽本人,在那之后,也都没活几年。白起第二年即被逼自杀,项羽到底年轻,时间稍长,又活了五年。结局大家都知道,自刎于乌江,也是自杀。
这其中,是否有些一脉相承的道理呢?
经过一年休整,第二年十月,白起平定了上党郡。赵军刚刚遭遇灭顶之灾,是一鼓作气、灭掉赵国的良机。白起命令王龁攻占皮牢,就是今天的山西河津;司马梗攻占太原;他自己准备亲率大军,直捣邯郸。
消息传出,韩赵两家举国震动。他们立即派出说客苏代,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,去贿赂范雎。这一下有好看的了,苏代是舌辩之士,范雎也靠这个起家。两条伶俐的舌头相遇,到底哪条鼓动得更快?
苏代说:“赵国一旦灭亡,秦王就可以称帝,武安君一定会封为三公。他为秦国夺取了七十多座城邑,南边平定了楚国的鄢、郢及汉中地区,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,即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、召公和吕望,功劳也无非如此吧。如果赵国灭亡,秦王称帝,那么武安君位居三公是确定无疑的,您能屈居他之下吗?即使不甘心,也没有办法。秦军围困上党,上党的百姓都转而归附赵国。天下百姓谁都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。如果灭掉赵国,它北边土地将落入燕国,东边土地将并入齐国,南边土地会归入韩魏,您所得到的百姓也没多少。照我看来,不如趁着韩国、赵国惊恐万状,让它们割点土地,免得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勋。”
这话打动了范雎。他立即向秦王建议,秦军疲惫不堪,不宜继续作战。秦王对范雎早已言听计从,立即同意接受韩国和赵国割让的城池,罢兵言和。
单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,白起指挥进兵时机正好,功在国家;范雎建议退兵私心甚重,误国误民。白起听说后,极度不满,从此就对范雎有了看法;范雎呢,对功勋卓著的白起,也起了戒心。在这一点上,白起近乎廉颇,而范雎则大不如蔺相如。将相不和,伤国本,害自身。
却说赵国,本来答应割让六座城池,后来又突然毁约。秦王大怒,于公元前258年二月再度兴兵,进攻邯郸。这时正值白起生病行动不便,没法出战,秦王就派五大夫王陵作为主将。王陵打了一阵子,没取得什么进展,秦王派兵过去增援,还是不见效果。这时白起身体痊愈,秦王想起用他,但白起不愿意。他说:“打邯郸没那么容易。各个诸侯国对秦国积怨很深,每天都有援兵到达。秦国虽然在长平消灭了赵军主力,但秦军也损失过半,国内兵力空虚。远行千里越过河山去攻打别人的国都,赵军在城里抵抗,诸侯军在城外攻击,里应外合,内外夹击,必定要击败秦军。这个仗不能打!”
#p#副标题#e#范雎说完这些,就喝退须贾,然后进宫报告秦王,建议接受魏国的和议请求,但拒绝须贾这个使者,责令他立即回国。须贾离开之前,来向范雎辞行。范雎大摆筵席,把各个诸侯国的使者全部请到大堂之上,摆满丰盛的菜肴,却让须贾坐在堂下,面前摆着铡碎的草和豆子,左右分别坐一个受过黥刑,就是脸上刺了字的犯人,拿马料喂他。范雎还数落他说:“回去告诉魏王,马上把魏齐的头送来,要不,我一定要血洗大梁!”消息传回魏国,魏齐相国也不当了,抛下相印,悄悄逃离魏国,跑到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那里,寻求庇护。
范雎在秦昭王跟前确实得宠。秦王决心替范雎报私仇,就给平原君写封信,说:“久闻大名,听说你有情有义,我很想跟你交个朋友。请你来看我,咱们俩痛痛快快喝他十天半月的。”普天之下,谁不畏惧暴秦?再加上秦王送来的高帽子,平原君也深以为然,于是就兴冲冲地一路西行,来到秦国。
秦王没有食言,跟平原君喝了好几顿酒,然后才摊牌。他说:“过去周文王得到吕尚,尊他为太公;齐桓公得到管仲,尊他为仲父。现在范雎就像我的叔父一样。他的仇人藏在你家,请你交出来,要不然别想出函谷关。”平原君说:“魏齐是我的朋友,就是在我家,我也不能交给你,何况还不在呢?”秦王不跟平原君啰唆,直接找到赵王。这时赵国国王是赵孝成王,名叫赵丹。秦王告诉赵丹:“大王的弟弟在我这里,范雎的仇人在你弟弟家。如果你不快点把魏齐的头送来,我马上派兵进攻赵国,你弟弟也别想出函谷关!”赵王闻听,立即派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。魏齐抢先一步逃出去,找到赵国的丞相虞卿。虞卿这人,也不知道犯了哪门子邪,也丢下相位,带着魏齐,又跑回魏国,向信陵君求援,打算逃往楚国。在这事上,秦国固然过分,但魏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,为他背井离乡,实在不值。
正因为如此,信陵君虽然名声在外,心里还是犯嘀咕。他说:“虞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正好候赢在旁边,他说:“虞卿从前没发达的时候,赵王见了第一面,就赐他白璧一双,黄金百镒;见第二面,拜他为上卿;见第三面,拜他为相国。那个时候,天下人谁不知道虞卿?现在魏齐有困难,虞卿毫不犹豫,抛弃高官厚禄,跟他一齐逃亡,您还问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人确实很难了解,了解别人也不容易啊。”这话绵里藏针,信陵君听了非常惭愧,赶紧驾车,出城迎接。魏齐这家伙总算识趣了一回,知道信陵君态度犹豫,就自己抹了脖子。
这是睚眦之怨必报。一饭之德必偿,须贾能保住性命,也算例子,但还不止于此。郑安平救过范雎的命,王稽带他来的秦国。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发达,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范雎登上相位之后,王稽就过来求官。这事不难,秦王很给面子,封王稽为河东太守,特许他三年不必汇报工作;提拔郑安平当将军,让他带兵增援王龁,继续围攻邯郸。
荐举贤能,充当重任,本来是相国的分内职责。范雎举荐的这两个人,到底有多贤能呢?按照他的聪明劲,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。可是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:郑安平带兵攻赵,战败投降;王稽与别国私通,最后被砍头示众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郑安平阵前投敌,发生在白起两次抗命之后。范雎之所以如此积极排挤白起,恐怕不能说跟这事毫无关系。
看到这里,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白起的名将名副其实,范雎名相徒有其名。说起来,范雎对白起“言而杀之”,其实也是“睚眦之怨必报”的表现。白起不是闪过他的面子嘛。事后还说了点风凉话。一饭之德必偿,可算美德;睚眦之怨必报,确是恶习。这样的行为,说白一点,就是哥们儿义气。在街面上混世界,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,也许能混成个大哥;再宽一点,当个县官儿也行,主宰一州的军民事务,就可能捅娄子,宰相确实不能胜任。
关于举荐人才,流传最广的美德人物,当属祁奚。祁奚字黄羊,春秋时期在晋国任中军尉,后来上了岁数,要求告老还乡,晋悼公问他:“谁接替你的职位比较合适呢?”祁奚说:“解狐可以。”晋悼公笑着说:“解狐可是你的仇人啊。”祁奚说:“主公您问的是谁可以接替中军尉,而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!”后来解狐死了,晋悼公再度向祁奚征求人选,祁奚说:“祁午可以。”晋悼公很惊奇,说:“祁午不是你儿子吗?”祁奚淡淡地说:“主公问的是中军尉人选,并没有问谁是我儿子。”
#p#副标题#e#这就是“外举不避仇、内举不避亲”的故事。其中的解狐,确实是个耿直之士,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,出任上党郡守。邢伯柳过来感谢,解狐说:“举荐你,是为了公事;怨恨你,是个人私情。你走吧,我对你的怨恨,并没有改变!”这人就是耿介如此,可见祁奚没有做错。当然,祈午的表现,也非常令人满意。
祁奚的表现,近乎圣人。心向往之,实不能至,有借鉴意义,但缺乏可操作性。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位宰相,唐朝的裴度,面对故旧求官时的反应。请注意,那个求官者,道德上并无瑕疵,还是个忠厚君子。
这事记录在《唐语林》中。说的是裴度当宰相以后,对以前没当官时的朋友,以及有恩于己的人家子弟,积极举荐报答,从来不曾忘记。大臣中有个品德无可指责、平常没什么话的人,突然说:“我和谁谁谁,跟裴晋公都是老交情。从前没当官时,我们有过约定,不论谁发达了,都要互相扶持。我从政多年经验丰富,裴晋公却一直不肯重用。”这话传到裴度耳朵里,裴度对传话的人笑笑,说:“我确实负了约。你见过灵芝、珊瑚吧。”那人说:“灵芝、珊瑚,都是稀世珍宝。”裴度又说:“你游玩过山水吧?”那人说:“名山大川游了很多,只有庐山瀑布像银河,举世无双!”裴度说:“灵芝、珊瑚都是珍宝,但要盖房子,还是得用樟木、楠木、桤木;瀑布可以入画,但对百姓生活没有帮助,要灌溉良田,还是得河水。那个人的德行文章、气度举止,可以作为大臣的表率,谁看了都会尊敬,但是长厚有余、机灵不足,而且懦弱多疑。从前人民质朴,地不过千里,官不过百员,内无权臣作乱,外无奸诈祸害。画地为牢,人不敢逃;只用穿赭衣作为惩罚,人们就不敢犯罪。虽然叫列郡建国,分封侯爵伯爵,可即便是大国,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,很容易治理。现在天子设置一万八千个官职,三百五十个郡,四十六位将帅,八十万大军,礼乐文物、官员士子,都远远超过古代。如果没有王佐之材,我怎么敢随便举荐他呢?”
《唐语林》不是正史,此时不能完全坐实,但其中的道理,大抵不错。一句话,要量材使用。可是,范雎举荐郑安平和王稽,做到这一点了么?郑安平败仗可以理解,投降不能原谅;至于王稽,里通外国,更是让人无法接受。按照秦国的法律,荐举失察,要负同样的罪责,范雎应该被夷灭三族。但是秦王的宠幸还没过保质期,所以丝毫没有追究。
范雎推举私人、谗杀大将,毫无疑问,都是将个人好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。说白点,他并没有为秦国效力的真心。他为秦王分析天下形势,制定“远交近攻”、“固干削枝”的策略,根本目的,都是为了个人地位,而非为秦国统一天下。当然,我们这么要求他,可能也有点超出时代。战国时期,人才流动非常频繁,一不高兴,抬起屁股就可以走人。“楚才晋用”这个成语,就是那种局面的产物。所以说,当时的人们,很难有祖国的观念。祖国观念都没有,你还要求他为别的国家效忠,这怎么可能。
如果我是范雎,也许不会滥用私人、谗杀大将,但也很难真心为秦国效力。秦国是什么?秦王,还是那一套官僚机构?反正国家是大片的泥土,不会说话;人民是遍地的农人、贩夫走卒,会说话但没人听。效力最大的,就是那一套独裁统治。它像一架巨大的机器,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。总体而言,没有人能独立改变机器的运转,每个人都制人,也制于人。其实,王稽向范雎跑官时说的那番话,还是蛮有水平的。他说:“有三件事无法预知,三件事无可奈何。秦王某天晏驾,是第一个无法预知;您突然归西,是第二个无法预知;我暴病死于沟壑,是第三个无法预知。一旦秦王晏驾,您再恨我,也无可奈何;如果您突然归西,您再恨我,也是无可奈何;假如我暴死沟壑,您再恨我,还是无可奈何。”意思很明白: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。趁现在秦王还宠信你、我还年轻有精力能折腾,赶紧给我个官儿当当吧。
说这话水平高,是因为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:上有独裁之君,下有专权之臣。算是相辅相成,类似磁铁的南北二极。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时代。
风筝飞得再高,总有一只手,在地上牵着。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大将再勇猛,将士再顽强,最后还是要输在案牍文书手中。这就是白起们的命运。然而,在这一整套以独裁为基础的官僚机制里,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他们的斗争,基本上是零和游戏:秦王拖延了灭赵的时间,增加了战争成本;白起丢掉了性命;范雎丧失了名誉。尽管他最后在蔡泽的劝说下,急流勇退,落了善终,但谗杀大将的恶名,却永世难消。只要《史记》不失传。人们就会一代代地铭记下去。
不是么?
相关内容